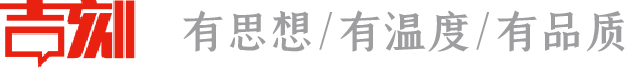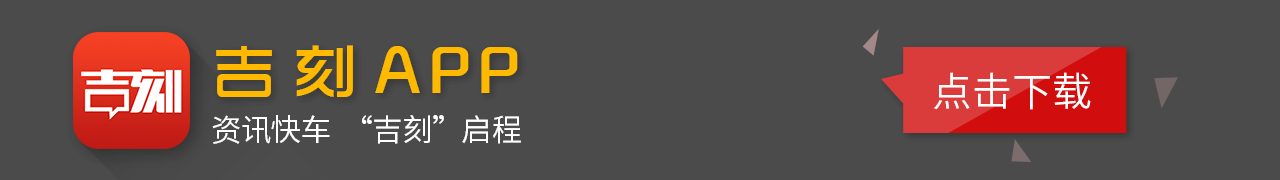任何一位作家,都必须面对一个文化坐标。细看中国历史,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群是真正的安土重迁。一波又一波大小移民潮,从东到西、从北到南,不断地彼此混合与彼此影响,终于同化成一个具有巨大向心力的中华文化圈。
不要轻视各地那些小异的文化。那些特色,是适应当地风物与民情,历时间之久孕育而成。在长白山地区,穹庐的居民驰骏马于平川,引长弓射大雕,而树林里的猎人养育巨大的海东青(一种猎鹰),射鹿刺鱼,获取他们的食物,以“九腔十八调,七十二嗨嗨”唱着东北的岁月。只有将斯雄的《长白九章》放在这样的谱系中,才可以理解其文本携带的气息、症候与美学。
斯雄的《长白九章》以“外乡人”的视角,书写了一段吉林文化之旅。全书共九章,以“松花湖上话摇篮”开始,以“燕麦的精神”结束,构成了一幅当代长白文化图景。这一图景,首先是社会学的。第一章《松花湖上话摇篮》,写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大坝及其重建,展现的是政策支持下我国水电建设管理进行的积极探索。第二章《粉雪之乡》,则描绘了北国风光,冰天雪地渐成金山银山。《四访查干湖》《玛珥湖畔》等章节,聚焦生态保护。《黑土地上玉米香》《燕麦的精神》《走向餐桌的人参》《不舍“二人转”》等,则以物象呈现吉林的习俗。
作为东北文化的典型聚集场所,我毫不怀疑《长白九章》能有如此多的“戏剧性”。实际上,“戏剧性”是一个过于学院化的表达,而真实的情况是,这些“戏剧性”不过是吉林乃至整个东北的日常。斯雄正是通过散文的写实方式,将吉林文化的日常样貌呈现到读者面前。需要注意的是,“非虚构”并非意味着与现实完全同一。与之相反,只有通过艺术的归纳,才能为“现实”赋形。亚里士多德有句古老的诤言,“艺术模仿自然”——模仿的意思并非复制,而是创造。也就是说,社会学的内容必须配合恰当的诗学形式,才能将文化的本真呈现出来。
在笔者看来,斯雄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真诚,同时也有文学的创造性和表现力。在《长白九章》每篇文章中,斯雄几乎都会强调一种人文的情感。具体来说,他以特有的历史、人文、风物、逸事为中心,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,建构了一个诗学的长白。
与此同时,斯雄在叙事的成规下还创造了他的表达。他借长白文化成就了他的语言修辞,这来自长白文化的整体形态,更来自故事背后作者并非只是“隔岸观火”,而是以现代性的眼光将当地风物文人式地“景观化”。或许可以用一个特殊的词来描写这种关怀——“回心”。“回心”又作“迴心”,原本是指皈依。在《长白九章》中,则是指社会学和诗学文本完成了对话,而且在个人逻辑(情感性)与文化逻辑(必然性)之间,斯雄最终选择了个人逻辑来展开他的思考和书写。例如在《粉雪之乡》中,笔者喜欢的一段:《北国之春》打动我的,是寒冷之下的温馨躁动,如今,是“北国的春天已来临”。的确,粉雪之乡不“猫冬”,残雪正消融,闻见了“微微南来风”。
正是在这样的“微醺”之下,斯雄完成了对当代吉林文化的书写。
(作者:丛文君 史册,史册系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〔新闻学院〕副院长、教授,丛文君系该校博士研究生)
来源:光明日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