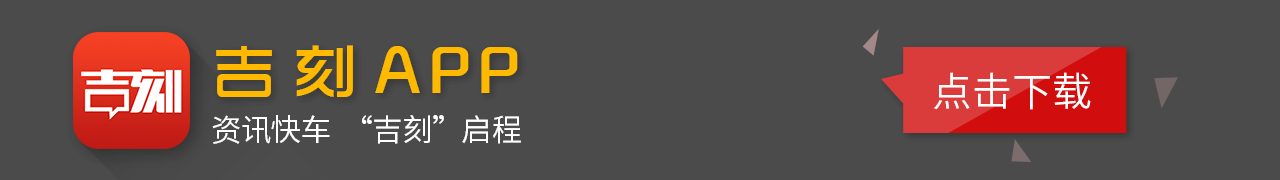“我们所在的(长春)市图书馆位置,过去就是伊通河的支流之一,地势很低,一直从地质宫慢慢流过来,向东注入伊通河。它,本身就是一条绿带,曾经大概有四条绿带,到现在基本上都不存在了。同时,伊通河的面貌重大变化,它现在基本上成为一条孤独的河流,没有支流。”
在第14期长春城市规划大讲堂上,长春广播电视台《发现长春》编委会编委、栏目历史顾问曹冬雁先生用了这样一个生动的开场白,讲述伊通河。
他演讲的主题为“再现母亲河——伊通河的生态履历”,地点在长春市图书馆文化讲堂。
从“害河”到“脏河”
从演讲主题,就能看出来,曹冬雁所要讲的,有关于伊通河的“生态”。
演讲开始前,他还特意强调,所讲的伊通河以长春市城区段为主。
“毕竟,它见证了城市的发展,也跟我们的生活更为密切些。”曹冬雁解释。
第一部分演讲,内容设定为从“害河”到“脏河”。
关于伊通河和长春市发展的关系,曹冬雁说,概括最好的就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、也是长春市地方史研究的先驱于泾先生的一段话:“1000多年来,在伊通河出现了扶余王城那样的历史名城,到了清代,形成了伊通州、长春厅和农安县三个城镇,至今则为一市两县,都在河畔。长春市伊通河畔也是柳条编外最大的城市,历史上的辉煌和精神都是和这条河流分不开。”
在于泾先生标点的《长春厅志》中记载:“长春厅境之水松花江,之于河则伊通河尽在城中。康熙年间,伊通河设有运粮船百余支,想见当年河流之巨,今则策马可渡。”这里说的康熙年间,大约是指1683年前后,与清志成熟时间相距200年。这200年间,伊通河的水文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无论是从宽度,还是从深度。
还是在这本《长春厅志》中,也记载着“平时水浅三尺,阔仅数丈,不利舟济。”同时,用较多的笔墨描述:“年久淤塞,不加疏浚,病民伤农,危害甚重。”
伊通河,逐渐从一条运输的航道变成一条经常发水,淹没村庄的河流。
曹冬雁还特意提及有关度量衡标准的细节。他说,清代时的一尺,相当于现在的0.32米;一丈,相当于现在的3.2米;运粮的一担,在那时是100~120斤之间,当年能装粮食最多的是2万2千斤,大约10吨,相当于“老解放牌”两辆还多一些,可见当年伊通河的吃水程度还是很大的。
后来,关于伊通河的记载主要是“危害甚烈”,成为一条灾河。
有资料可查,新中国建立以来,尤其是前50年,伊通河城区段特大洪涝灾害17次,平均不到3年。
“这个数字与长期历史的数字是吻合的。”曹冬雁也做了比较,1865年到1985年120年间,一共发生洪涝灾害38次,平均也是3年一次。从清代中期以后,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,洪涝灾害频率大体是相同。
“在座的很多老长春,对当年伊通河危害甚重,泛滥两岸,造成了的巨大的财产损失都有记忆。”曹冬雁讲起了他看过的一些老照片,他印象深刻的是,“就是在新华印刷厂旁边,拖拉机都陷里去了。”
到2000年之后,总体看伊通河泛滥成灾不是一个主要问题,而是逐渐转化成生态问题。
“不是说2000年之前这段时候没有生态问题,只不过是洪涝灾害更加紧迫、更加严重,掩盖了生态问题。”曹冬雁特意解释了一下。
在他看来,现在伊通河生态问题主要是,生态还原的问题,核心是恢复这条河流作为一个生态载体的自然属性。
目前,他一直追踪着长春市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。
“生态治河。”这个提法,让他很是期待。
“今天人们在伊通河的问题上基本能达成一致,生态或者河流作为生态的基础性载体,必须尊重自然规律,必须尊重大自然的和谐属性,否则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”曹冬雁表示,今天治理伊通河,对待自然环境,人与自然这种和谐相处,尊重大自然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。
伊通河的生态履历
对于伊通河的生态履历,曹冬雁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描述,“简单的素描,沉痛的教训”。
他说,他曾看过一本1959年出版的《大学地理学生参考书》,书中有一个章节介绍各个省会城市,它是这样表述长春的,“长春不仅是一个工业城市,而且还是一座美丽的公园城市”;一位罗马尼亚的朋友这样形容长春,“如果它没有高大的厂房和林立的烟筒,整个城市简直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园。”
这是1959年大学教科书里对长春的描写。
书中还写道,“在斯大林大街两侧有风光秀丽的胜利公园、人民公园和南湖公园,每天傍晚和假日迎接全市的职工游玩。”
曹冬雁解释了一下,人民公园,说的是现在的儿童公园。
“那个年代的长春,在生态底子上,还是非常厚的。”曹冬雁感慨了一句,那个时候,伊通河还是“鱼刺状”的,有四条“绿带”。就连南湖公园,都是以备用水源地出现的。
还是勾勒一下伊通河的生态履历吧!
1949年-1958年时期,虽然长春展开了工业建设,一些大型企业出现了。但在曹冬雁看来,由于多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,那个时期总体来说头脑比较冷静,比较实事求是,对于生态的破坏没有那么严重,规模不是太大。
1958年以后,进入大跃进时期。这个时期的伊通河,修了各种各样的中小型水库,在伊通河的上游有很多,标准很多,有的才10年一遇,后来小水库基本都放弃了,但是把河流弄得支离破碎。河流跟生态的肌体一样,是个完整的系统,不能分离,结果行政分割生态,支离破碎,破坏很大。
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前,这个时期仍是把重工业放在一个城市发展的(最)重要地位,轻工业也有一些上马。据资料,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,长春市几乎99%的工业废水,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伊通河。它不仅导致伊通河污染,而且是整个地下水,还有公园里的湖泊、水库里的水,因为它是一个系统。长春市缺水的城市,当年认识问题的科学手段很差,把一些认为污染不严重的水灌溉农田,又造成土壤的污染。
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,属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。“人民确实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,但代价依然很大,尤其是生态代价。”曹冬雁表示,这个时期的高度发展有生态遭受污染的历史必然性。但横向比较同一时期,我们的代价比人家多,透支严重。
总体来说,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之前,伊通河水质正常稳定,水生植物很多;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,水体污染严重,水生植物明显减少,鱼虾很少看到,有少量的浮游生物;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,排污越来越严重,大量水生生物灭绝,伊通河长春城区段终于成为最大的污水排放口;到了1985年大水之后,伊通河主要侧重于防洪。
“生态问题,有重视,但一直没有得到高度重视。”曹冬雁感慨,现在伊通河的几条支流大多数都已消失了,造成本应该是鱼刺状的河流变成了一条孤独的河流。
中国吉林网记者 王小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