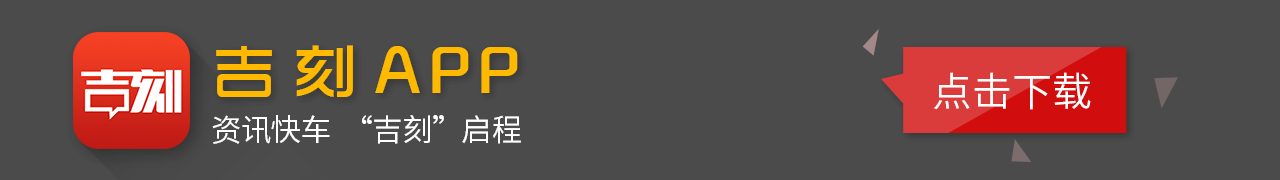故事三
那年的琦琦
琦琦的康复进展,没有东东和大宝快。
在一个地下室生活,来自长岭县的母亲于淑超,心情给外沉重。
3月末的地下室,格外的阴冷。蜷缩着身体,坐在床上,看着钟表指针,就这样一直看着,不出声的看着。

琦琦特别容易起湿疹,于淑超给孩子擦身子。 中国吉林网记者 郭全忻 摄
时间退到2011年,那年的7月27日,琦琦出生。
躺在妇产医院床上的的于淑超,清楚的记得,在病房的里的一幕。亲朋好友,围城一个圆圈,看着琦琦,逗着琦琦。
“孩子爸爸,给了我一个大大拥抱,因为儿女双全了。”于淑超说,之前和丈夫生了个女儿,这次又添个儿子,能不高兴吗?
琦琦出生的第一个新年,于淑超和丈夫,到城里的市场中,卖了不少平时不舍得吃好东西。
“儿子出生了,咋得都不能差了。”于淑超说,那个春节过得非常美满,一辈子都会忘记。
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,她和丈夫也做起了规划。
“等孩子在大些,我们就到城里打工,趁着年轻,多给孩子攒点钱,给孩子未来铺路。”于淑超说,吃苦不怕,只要能赚钱,再苦也值得。
不过,这种美好的设想,最终并没有实现。
不幸的消息
和女儿的活泼不同,琦琦长到两岁时候,开始表现出一些异样。
于淑超通过观察发现,按照以往经验,到了这个年龄,同龄的孩子已经咿呀学语。
可是在琦琦身上,却没有一点迹象。
“全家人都逗他,可是不论怎么引导,琦琦都没反应。”于淑超说,当时想想,可能孩子情况不一样,没准过段时间就好了。
等待,等待,再等待。
差不多又过了半年,琦琦没有改变。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他开始变得反常古怪。
此后,亲属也看出了问题,建议去省城医院做检查。
“这个时候不但不说话、不看人,开始烦躁易怒。”于淑超的心中充满了担忧和恐惧,为了弄清原因,全家来到长春。
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。
经过一系列检查,医生将其确诊为孤独症,并补充说道,因目前科学界无法查明病因,并没有特效药物。
医生的话字字如针,刺痛这位母亲的心,她不敢想儿子的未来,也不敢想自己的以后。
理想抵不过现实。面对无法改变的事实。
四处打听办法的于淑超,在听说孤独症患儿可以通过康复训练,使孩子今后生活能简单自理后。
这一点希望,成了其前行的动力。
二个角色的母亲
左手女儿,右手儿子。
因丈夫在老家,工作脱离不开,带孩子不方便。
2015年3月18日,于淑超带着女儿,儿子,来到省内一家康复医院,从此开启城市中漂泊。
和邻居们生活略有不同,在这座城市里,她的母亲身份要不断转换。
每天凌晨5点,她起床做饭,给患儿穿衣喂饭,还要给女儿梳头,之后匆匆喝几口剩粥,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出家门。
先送女儿上幼儿园,再送患儿去康复中心,从上午7点55分到下午3点10分,全程陪琦琦上完7节课,再带着儿子去幼儿园接女儿。
到家后,先让女儿完成作业看护琦琦,于淑超挤出时间收拾屋子、做晚饭,睡觉前还要帮助小冬作康复训练......
一天到晚,如同陀螺一样高速运转,累得腰疼腿酸,透不过气。
超强度的劳累,使于淑超积劳成疾,31岁的年龄,就患上了心脏病、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。
因为时常着急上火,4颗牙提前“下岗”。
于淑超为了儿子的康复,几乎耗尽了全部心血。
解脱的“尼古丁”
常言说,有啥别有病,没啥别没钱。然而这个不幸的家庭却是既有病又缺钱。
丈夫的微薄的收入,眼下已经无力支付康复费用。
于淑超坦言,在长春生活、治病,每年至少需要6万元。这几年,已经花光了家中的老底,又求亲靠友抬了两万多元,目前已是求借无门,说不定哪天就得被迫放弃治疗。
孩子的病没有好转,孩子学业,未来,无影无踪。
源于精神、病痛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,于淑超时常徘徊在绝望的边缘,从此开始粘上了香烟。
用她的话说,人绝望的时候,需要香烟解脱,最多时一天吸两盒。
“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,如果哪天死了,孩子可咋办。”此时的于淑超,对着地下室的半截窗,放声大哭。
而在此时,地下室另外两户邻居屋子里,也传来了同样的哭声 。
(应采访者要求,文中东东、小宝、琦琦为化名)